亏损超2亿,上海贵酒还有未来吗?
编辑 | 虞尔湖
出品 | 潮起网「于见专栏」
在过去的2024年里,白酒市场可谓是冰火两重天。茅台、五粮液、汾酒等一线酒企营利双增,而二线酒企们则明显掉队,深陷经营困境。近期酱酒新贵岩石股份公布了2024年年报,报告期内营收2.85亿元,同比下滑82.54%;归母净利润亏损2.17亿元,同比下降349.63%。
在年报公布的当天,岩石股份还发布了一份公告,因2024年扣非净利润为负值且营收低于3亿元,触及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,公司将于4月23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
对于这一结果,很多投资者并不感到意外。早在1月份,岩石股份在业绩预亏公告中就提及在2024年年报披露后会有“戴帽”的可能。作为二级市场最有名的“不死鸟”,岩石股份再次来到退市边缘,这次还会创造浴火重生的奇迹吗?
雷声滚滚,业绩变脸
上市公司改名字屡见不鲜,不过像岩石股份这样改名换姓如同家常便饭的,却是少之又少。1993年经营建筑陶瓷的福建豪盛成功登陆上交所,成为“泉州第一股”。然而上市不到4年,福建豪盛业绩急转直下。
2001年利嘉集团对福建豪盛进行资产重组,入局房地产市场,公司名称变更为利嘉股份。重组后抱紧房地产大腿,本应该扶摇直上,不想却成为动荡的开始。
2006年利嘉股份证券名称变更多伦股份,因四处拿地导致资金链吃紧,实控人陈隆基萌生退意,开始寻找下家。2011年资本玩家李勇鸿入主多伦股份,不过仅7个月后便匆匆离场,随后律师大佬鲜言成为接盘侠。
2015年多伦股份发布公告,拟将公司名称变更为“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(上海)股份有限公司”,进军互联网金融领域。然而因虚假申报、采用多种手段操纵公司股价、鲜言被13名投资者告上法庭,并以“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”被刑拘,匹凸匹再次迎来新东家。
2016年,上海五牛成为匹凸匹新实控人。2017年为摆脱“P2P”不良影响,剥离互联网金融业务,公司名称变更为“上海岩石企业发展有限公司”,也就是现在的岩石股份。
初期,岩石股份业务主要以金属材料、能源化工等大宗交易为主,同时开展融资租赁和商业保理业务。2018年开始涉足白酒销售,2019年酱酒赛道大热,岩石股份宣布放弃贸易业务,转战白酒行业。
纵观这二十多年的发展,岩石股份可谓跌宕起伏,换了无数个马甲,先后涉猎建材、房地产、互联网金融、贸易等多个领域。就当外界认为入局白酒的岩石股份终于不再变形稳定下来,不成想依旧缺乏幸运的加持。
2023年12月,国内知名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海银财富发布公告,受经济下行影响,公司分销的部分产品出现赎回问题。而海银财富董事长韩宏伟和岩石股份实控人韩啸恰好是父子关系。
2024年9月更坏的消息传来,因涉嫌非法集资,韩宏伟及海银财富多名高管被警方带走。随后岩石股份发布公告,公司实控人韩啸受海银财富牵连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受此影响,岩石股份股价跌停,供应商、银行纷纷讨要债款。
今年3月,因韩啸未按时实施股票回购,上交所对岩石股份公开谴责,并要求进行整改。很明显,在海银财富暴雷后,岩石股份遇到了资金危机,其白酒生意也陷入“停摆”状态。
班门弄斧,金融卖酒
白酒行业十年一繁荣,五年一调整。周期之下有压力也有动力,很多白酒新贵都想抓住机会实现逆袭,岩石股份也是其中的一员。2017年酱酒成为新风口,岩石股份先后收购了江西章贡、贵州高酱两家酒企,试图在酱酒赛道大展拳脚。
做生意,自然要有个响亮的名字。2019年11月,岩石股份宣布更名,以“上海贵酒”闯荡白酒市场。不过更名后,上海贵酒并没有迎来开门红。当年12月洋河股份旗下的贵州贵酒以商标侵权为由,将上海贵酒告上法庭。
直到现在这场商标纠纷仍未停止,去年贵州贵酒再次起诉上海贵酒,索赔1亿元,这也导致其证券简称还在沿用岩石股份之名。与此同时作为白酒新势力,上海贵酒也并未被传统白酒企业们认可。
相比宣酒、肆拾玖坊、珍酒这些异军突起的新势力,上海贵酒的经营管理方式太过新潮,以至于在传统酒企眼中就是个另类。实际上,自成立之初,上海贵酒身上“酒”气并不多。
例如前任总经理鄢克亚、高利风、副总经理吴建诚尽管工作履历非常丰富,但均没有白酒行业管理经验,反倒都和互联网、金融、保险打过交道。至于上海贵酒背后的韩宏伟父子,更是以金融起家。
金融人做白酒,自然和传统酒企不一样。鄢克亚在任期间曾不止一次说过,上海贵酒不是卖酒的,而是一家品牌管理公司。高利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曾表示要学习华为的组织能力、学习宝洁、可口可乐的产品研发理念,学习保乐力加、帝亚吉欧先进的销售方法。
通过这些高管的发言就可以看出上海贵酒是非常矛盾的。既然做品牌,走轻资产模式就好了,干嘛还要斥巨资收购酒企?向通信、快销、洋酒巨头看齐,唯独不愿意和茅台、五粮液学习,那怎么在白酒行业做到知己知彼?
虽然上海贵酒的管理层善于包装,精于运营,确实在白酒赛道打造出了差异化,不还是在延续着白酒企业重营销的老路?频繁赞助《中国好声音》,独家冠名央视《品牌大国》节目,大屏广告登陆纽约时代广场。
这一套花式营销下来,直接让上海贵酒的费用猛增。2021—2023年,其销售费用分别为1.41亿元、4.54亿元和7.21亿元。诚然重营销是白酒企业的一贯做法,上海贵酒的想法也很现实,只要拿重金砸出知名度,就不愁销量。只是白酒赛道讲究细水长流,上海贵酒快消式打法只能红一时,并不能红一世。
好故事还需好品质
上个月全球顶流网红“甲亢哥”开启首次中国行,直播过程中不少人都想蹭一蹭流量,最终来自重庆荣昌的“卤鹅大叔”成功脱颖而出,实现了全网爆火。
想要红,蹭流量无疑是最快速的方法。初入酱酒赛道的上海贵酒同样选择了蹭热度。从取名“贵酒”,到推出以军旅文化为卖点的“军星”酒,都让上海贵酒成为白酒圈内热议的对象。
有争议自然有流量,上海贵酒至少迈出了成功第一步。不过想要把流量变现讲出好故事不仅需要渠道的支持,更考验酒厂的底蕴。然而在这两方面,上海贵酒和一二线酒企还有着天地之别。
场景化一直是上海贵酒渠道建设的重点,通过在全国一、二线城市建设体验中心,创办“六感沉浸”品鉴会来吸引消费者和经销商的关注。这一做法取得了十足的成效,2021年其经销商数量仅为300多家,到了2023年就增长至4429家。
随着经销商的裂变,上海贵酒营收也由2021年6.03亿元上涨至2023年的16.29亿元。按理来说,有如此广袤的经销商,上海贵酒在线下市场应当随处可见,然而尴尬的是,在商超、酒行都很难见到其产品。在线上电商平台,销量更是寥寥无几。
那么上海贵酒都卖给谁了呢?2022年,多名前上海贵酒员工在社交平台爆料,要求自掏腰包购买当月工资额的酒品,或者拉人头完成指标才能办理入职。
也就是说,上海贵酒是将员工发展为客户换来的好业绩。去年6月在回复上交所监管函中,上海贵酒首次承认关联方中国贵酒存在带单入职的情况,这无疑坐实了其销售成绩是虚假繁荣。
雪上加霜的是,随着酱酒市场退烧加上负面新闻不断,经销商们正在加速逃离。截至2024年底上海贵酒经销商只剩下772家,一年之内减少了3693家。
大量经销商流失,当然是不愿意承担风险,不过也侧面说明上海贵酒的产品力不够硬。目前上海贵酒有传统的天青、君道、高酱、君澜四大系列,还有面向年轻人群的十七光年果酒和最®酒光瓶酒两大品牌。
表面上产品内容十分全面,但更像是东拼西凑。例如天青月黄酒是高酱酒业生产,而天青16代礼盒中的月黄酒则是由黔醉酒业生产。实际上,上海贵酒的产能并不充足,不管是酱酒还是果酒,都需要靠外采来满足市场需求。
这就导致同一系列的酒品质完全不一样。而且在市场层面,大多数消费者对于上海贵酒的印象是,包装极好,但口感发酸偏苦,和郎酒、习酒等酱酒品牌有着明显的差距,说白了还是底子不行。
结语
两年前,在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105层会议厅,上海贵酒还意气风发,誓要走出国门冲向世界,用价值、文化和形象为向导,打造年轻化的一流白酒品牌。然而想得越高,跌的越惨。
在2025年报中,上海贵酒表示要聚焦重点品牌和重点区域,专注酱酒主业,加强线上线下双向发展。不过如今酱酒热度消退,躺赚时代已经结束,况且资金短缺之下,留给上海贵酒的机会已然不多。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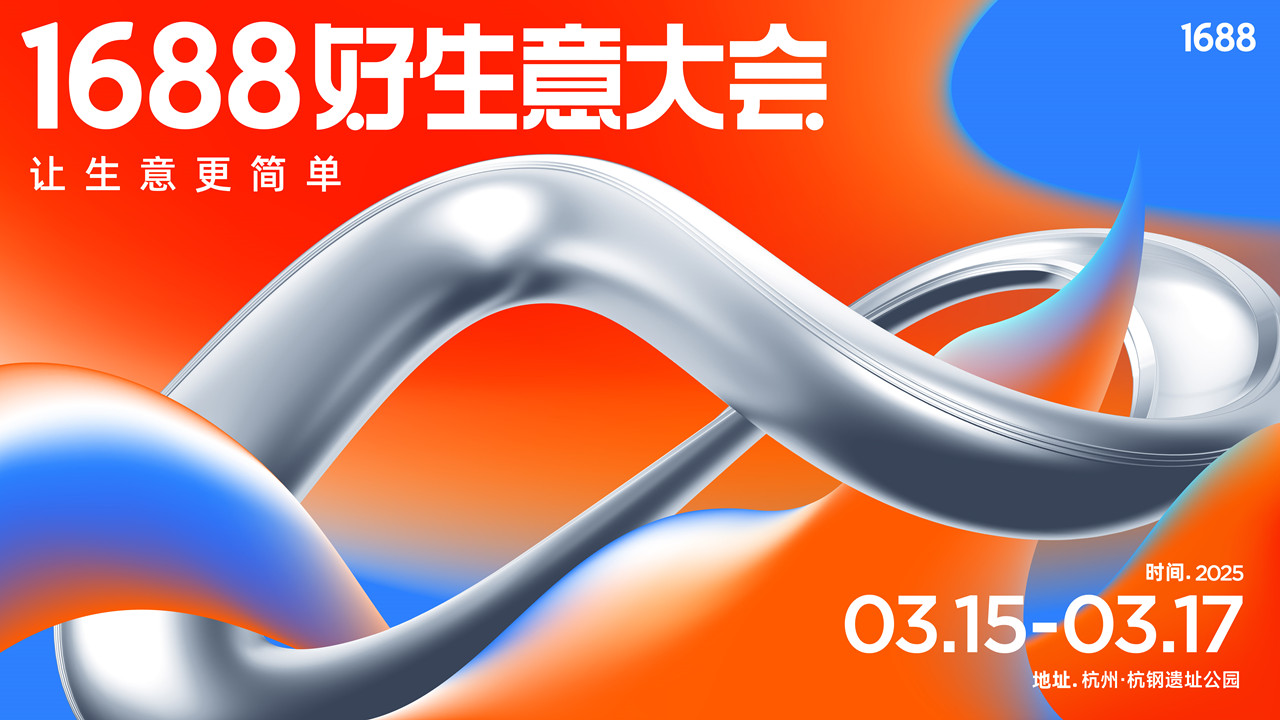
 加载中,请稍侯......
加载中,请稍侯......